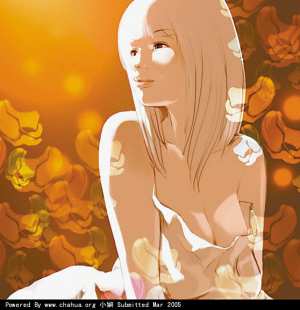|
 |
|
| 2007 年 6 月 27 日 星期 三 |
|
|||
|
| 昨日是国际禁毒日。今年禁毒日主题是“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近日本报记者探访戒毒所,体验—— |
| 戒毒所女民警的一天 |
20日7时55分,我来到位于310国道附近的洛阳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来体验戒毒女民警牛晓峰的一日工作。 干这,最累的是心 8时整,“干这个工作,身体的累还能忍受,最累的是心,压力太大!”牛晓峰边换警服边说。 虽然是大早晨,牛晓峰仍显得很疲惫,眼睑微肿。“打2001年戒毒所成立,我就来这儿当民警,一上班就是24个小时,生物钟都被打乱了。女人熬夜最容易老啊!” 话虽这样说,可一到了工作岗位,牛晓峰顿时精神抖擞。她和值班民警迅速完成了交接班,然后带着我到戒毒学员的各个宿舍内巡查。 “起立!”看到我们进来,正在低头忙活的戒毒女们迅速立正。女戒毒区的每个宿舍有6个上下铺,屋内有厕所。每层楼都被铁门锁着,戒毒女们就在这个相对封闭的区域度过每一天的戒毒生活。 地上放着几个大纸箱,箱内堆着金色的塑料叶,戒毒女们有的在忙着用胶水把“叶子”粘到“树枝”上,有的正在粘金色的小铃铛,几个宿舍形成了一个生产流程。她们在忙什么呢? “她们正在做手工艺花。”牛晓峰解释说,为了让这些戒毒女分散注意力,每天有事可做,戒毒所每天都给她们安排一些力所能及的手工活。 “看,这个女孩只有16岁。”一个女孩应声抬头——果然是一张未脱稚气的脸庞。 她朝我笑了一下。我的心猛然抽紧了。 在另外几个宿舍内,我又见到了两个18岁的女孩,清秀、单纯。如果在阳光下,这些脸庞该是多么美丽,可在这个有些阴冷的屋内,却是那么苍白,而且她们的眼神都略显呆滞,连眼珠都好像懒得动一下。 “她们看起来都挺顺从,挺有规矩的!”听到我这样说,牛晓峰摇了摇头:“不,她们表面平静,可你无法想象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她说,曾见过吸毒女毒瘾发作时,拿脑袋往床上撞;有的跑到厕所里,像掏洞一样在地上乱扒;有的睡到半夜,“咚”的从上铺摔下来;有的浑身哆嗦、流着鼻涕,抱着头往双膝间使劲埋……想尽办法自杀的,也不乏其人。 所以,在吸毒女的宿舍里,除了必要的生活物品,连根晾衣绳子也不会给她们留。在民警值班室里,监控录像24个小时监控每个屋内的所有情况。 “在别人睡觉的时侯,我们更得瞪大双眼,一点儿都不能掉以轻心!”牛晓峰说。 越呆,越觉得可怕 9时, 牛晓峰开始每天例行的单独谈话教育(如上图)。第一个谈话的就是那个16岁女孩骆新岩(化名)。她怯怯地推开门,怯怯地在板凳上坐下。 “我4岁时,爸妈就离婚了。初中毕业后,我跟着几个朋友玩,看见他们吸黄皮,很好奇,也想尝尝……进来后我才知道吸毒这么可怕。” “我们相信你,你吸毒量小,时间短,配合药物治疗一定会戒掉。出去后不要再与那些朋友来往了!” “牛管教,你放心,我没有上‘大道’(上瘾),我一定会戒掉!”骆新岩的眼泪不断涌出来,她拼命用手背擦着。 “这几年,像这样好奇无知而吸上毒的年轻人多得很。”牛晓峰皱眉。 “让你看看另外一个‘资深’吸毒者。”牛晓峰的第二个谈心对象是已经七进七出戒毒所的林茹红(化名)。 “林茹红是我市最早下海的那批人,1990年她和丈夫拥有资产100多万元,可1992年两人一起吸毒之后,人生就全改变了。” 听牛晓峰讲自己的故事,漂亮的林茹红没表情,但笑了笑。 “其实,加上我主动去戒毒的次数,我已戒了十几次了。”林茹红说,到1998年,100多万元的资产已经被她和丈夫吸完了。因为吸毒,他们不敢要孩子,于是就离婚,各吸各的毒。现在,她已到了“活着没信心,死了没决心”的阶段。 “每次她走时,都信誓旦旦说:牛管教,我绝对不会再在这个地方见到你。可没过多久,她就又出现在戒毒所里。刚开始我都不想理她。可后来我知道,面对毒品,吸毒人的意志太薄弱了。”牛晓峰说,人们对戒毒人员的歧视也是导致他们复吸的原因。 “有时候我异想天开,如果世上有后悔药,我一定要个小宝宝,和老公好好过日子。可是我这一辈子,别说当妈妈,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还能活多久……”林的一番话,让牛晓峰的眼圈红了。 “跟她们谈一次心,我的心就跟着灰暗一次。”牛晓峰说,越在这里呆,自己就越觉得毒品可怕。“只要一沾毒品,这个人就几乎是一只脚迈进了地狱。” 和两个人谈完话,已经10:30了。牛晓峰带戒毒学员到操场上跳绳。为了增强戒毒学员的体质,她们平时举行一些队形训练、拔河比赛等活动。 11:30,开饭了。牛晓峰跟着餐车到每个屋,给戒毒女们分饭,午饭是菜汤、馒头。她们大都吃得很香。 想走,又舍不得 15:00,牛晓峰带着戒毒学员李芬丽、张荣荣(均为化名)和家属会见。李芬丽18岁,皮肤白皙,长得特别水灵。她是被男朋友引诱吸上毒的,两个人双双被抓,强制戒毒。这一次,是她的好朋友来看她,好朋友哭得稀里哗啦,她倒没掉泪。 张荣荣40多岁了,有个孩子在读高中。这次她弟弟给她带来了一本电脑书和一本新华字典。“她很喜欢看书,精神状态也不错。看到她,我心里就觉得很有希望。”牛晓峰把书交给张荣荣,鼓励她:“多看看书,要想想孩子都快高考了,在外面等着你呢。” 在戒毒所接见大厅,有一个女子带着一个大约3岁的小女孩来看丈夫,小女孩双手托腮,瞪着大大的眼睛隔着玻璃好奇地看着爸爸,牛晓峰赶紧上前示意女子让孩子先到外面等着。“尽量不要带这么小的孩子到这儿。” 牛晓峰一边监督着被接见的学员,一边给我讲她见到的难忘事儿。 “一天有个8岁左右的小男孩来到戒毒所。我问:‘你来干什么呢?’他回答:‘我来看我爸妈,他们都在这儿关着。’‘你知道他们为啥关在这里吗?’小男孩的表情很漠然:‘知道,吸毒呗。他们不敢当着我的面吸,可我早就知道。’”说到这儿,牛晓峰的泪又在眼里打转儿。“小男孩的表情,我一辈子都忘不掉!” “我干了这么多年戒毒民警,都快有职业病了。见了亲戚朋友家里的年轻人,就对他们说:别碰毒品,一点儿都不能碰!我真的希望全社会都来‘抵制毒品,参与禁毒’。” 时间过得飞快,已经是18点了,我该告辞了。“真羡慕你们,每天见到的都是正常人。而我天天见的都是这些不正常人。在这里上班,跟关监狱差不多。”“你没想过换工作?”“想过,有时候真不想在这儿干了,可真要走,不知道为啥又舍不得。” “我得到明天早上8点才能下班。又一晚上见不到儿子啦。”作为3岁孩子的母亲,牛晓峰有些无奈。 我知道:今晚,对于她——一个戒毒女民警来说,又是一个无眠之夜。 文/本报记者 郑凤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