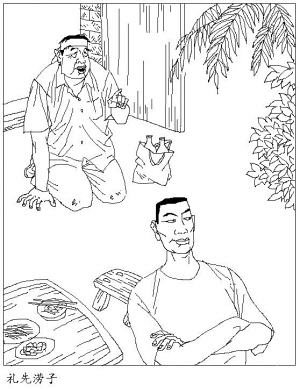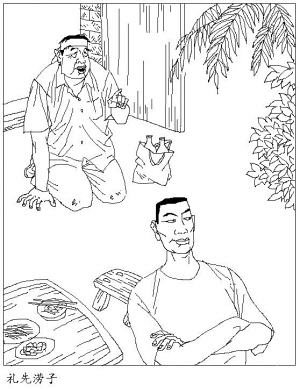 | | 李玉明 绘 |
|
在老街,有两种人受敬重。一种是能端国家饭碗,拿公家饷钱的人,老街人称之为有大本事;第二种是能为老街人拿事争面子的人,老街称这种人是有真本事。涝子就属于后者。涝子是靠主持红白喜事,凭真本事吃饭的“礼先”。
涝子出生那年天大旱,他娘便给他取了个湿漉漉的名字,希望涝子日后能旱涝保收,多捞银子。涝子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整日在家无所事事。涝子的五爷在老街开了一家纸扎店,专门经营祭奠用的各种纸扎制品。涝子的母亲就把涝子送到五爷的店里当学徒。
老街开纸扎店的不止五爷一家,可就数五爷的生意好。不是五爷的纸扎活做得好,而是五爷可以免费为办丧事的人家充当“礼先”。老街把操持红白事的人称为“礼先”。请个“礼先”是要花钱的。五爷偶尔也会被街外面的人请去做“礼先”,五爷外出给别人操办丧事就带着涝子。
涝子在纸扎手艺上没有多大长进,在礼道方面却极有灵性,两三回下来便能将做场的路数记个滚瓜烂熟。一次外出去做场子,出殡途中,五爷忽然中风,躺倒在地。办丧事的主家焦急万分,驴拉磨般团团转。涝子把五爷伺候停当,对主家说,莫着急莫着急,余下的事我来做。涝子不慌不忙,把余下的活做得有鼻子有眼。尤其是最后一场子的长拖音“跪——”是给街坊四邻听的,意思是告诉大家,主家的所有孝道礼事都进行完了。涝子把那声“跪——”拖得又长又亮,声如洪钟。主家大喜,竟给涝子包了50元的大礼。涝子那年只有15岁。
涝子有了名气,谁家办个丧事,都以能请到涝子做“礼先”而觉得长面子。来给涝子说媒提亲的人踏破了涝子家的门坎。涝子就是不吐口。娘急了,说,你到底是相中谁了。涝子说是华姑。娘说,你发癔症呢。华姑可是老街的一枝花啊,大户人家的闺女,谁敢去缠事?
涝子就敢。涝子想方设法和华姑见了几次面,华姑就死心塌地地要跟涝子,硬是退了街道办事处主任家的彩礼,挺着肚子和涝子拜了堂。办事处主任的嘴都气歪了,明着暗着没少摆治涝子,涝子全没当回事,见到主任就点头哈腰,献殷勤递烟跟个孙子似的。隔年,主任的父亲过世,涝子自然是主持,连环套的礼道真让老街人开了眼。
头天,主任咬着牙挺了过去,第二天就跪得双膝淤肿,头叩得分不出南北。大家都说主任是个孝子,哭得伤心,只有涝子心里有数,主任是哭他爹还是哭自己。天黑,主任拎着两瓶酒,一拐一拐摸进涝子家,“扑通”跪在涝子面前:“涝子,你个王八蛋,我服你了。看在俺死去的爹的份上,明天那些礼数就省了吧。”说罢给涝子叩了三个响头。事情传开,老街人对涝子又多了些敬畏。
涝子的名气如日中天,忽然出走离开了老街。老街人揣测,涝子出走肯定和霍家的丧事有关。霍家是老街的大姓人家,老街在外端国家饭碗拿公家饷钱的人,也数霍家的最多。霍家在老街很是牛气。涝子的名气再大,在老街人的心中也是排在霍家之后的。
霍家一位在外做事的大官员病逝,要办丧事。涝子闻后心中窃喜。你霍家人再风光,到头来还不是我涝子打发你上路?涝子换了新衣服,坐在里屋,对媳妇说,霍家人来找我,就说我不舒服。媳妇说,知道了,你得端端架子。霍家来人了,只是要了些花圈就走了,压根就没有提请人的事。涝子纳闷,走出家门去看个究竟。霍家宅院前已是人头攒动。院子里除了霍家人,还有许多城里来的男男女女。人们低着头,一脸的肃穆,年轻漂亮的女人嘤嘤抽泣,用手中飘着馨香的手绢擦着泪珠,与霍家不沾亲不带故却哭得真心实意。一个胖子气喘吁吁地念了一篇勤勤恳恳鞠躬尽瘁的文章,大家对着逝者的遗像三鞠躬,丧事就算办完了。
老街人直咂嘴,还是外边的人风光露脸。街道主任里外张罗着,故意推开涝子:别挡道,这里没你啥事!
涝子心里疙疙瘩瘩的,闷闷不乐地回家倒头就睡。第二天,涝子就失踪了。涝子失踪半月后给家里捎了信,说要在外混出个模样,不冲别的,就冲将来也像霍家官员那样排场地死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