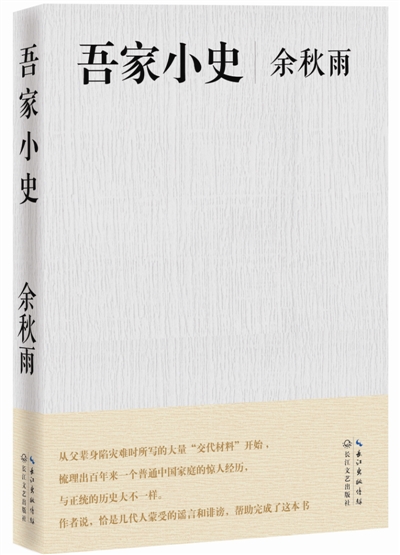|
||||||||||||||
 |
|
|
2014 年 3 月 10 日 星期 一 |
|
||
| 自家小史 娓娓道来 |
| 07 逃离,定居安徽 |
马兰大喜过望,却又忧心忡忡:“你这么一个纵横世界的文化人,陷在合肥这个小地方,会不会不方便?” 我说:“正因为纵横世界,哪个角落都可以安居。人为什么要结婚?就是为了走投无路时有地方逃,逃到老婆身边。” 比起上海,当时合肥还相当贫困落后。我们住在三里街一处简陋的宿舍里,我在那里写了《霜冷长河》和《秋千架》。 在合肥那几年,我心里很安静。妻子经常带着剧团到各地演出,一出去就演很多场。当时国内有几家报刊在全国各省作问卷调查,问民众最喜欢哪个剧种,最喜欢哪个演员。马兰领军的剧种和她本人,几次都名列第一。 不管她到哪个城市演出,都一票难求。即使在台湾大选期间,剧场外面每天晚上拥挤着几十万为选举“造势”的民众,没有一个剧团敢在这个时候卖票,而她的演出还是场场爆满。在大陆很多城市,她都创造了连续演出场次最高的纪录。戏剧危机,在她身上从未体现过。 她创造的最高票房,没有牵制她大胆的国际化实验。而她的实验,也没有影响她的票房。 她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戏迷,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联盟。如果她去北京演出,那个联盟的各地成员都会用各种交通方式赶到北京,由北京的成员负责接待。在这个群体的人,一律叫我“姐夫”。这一叫,使得踉跄于陌路上的我也稍稍有了一点安全感。 但是,最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妻子几次回家,表情郁闷地告诉我,不知怎么回事,周围的人突然都躲着她。 一位刚刚退休的省委领导悄悄告诉她:“他们的‘局’排定了,没有你。你还是走吧!” 她惊讶而又慌乱地看着这位领导,说不出一句话,只是在心里问:他们是谁?什么叫局?我为什么要走?走到哪里去? 那些日子,马兰只是等,她在等一个说法,但是她不问、不求、不争。她的人格和艺术水平,是由许多“不”字组成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打破。在等的过程中,她一直在猜测其中的原因,而且全在自己身上找。 “是不是那次北京官员来视察,我没有听从省里的意思去参加联欢会?”“是不是我从来没有向上级汇报过思想?”“是不是我宣布不再参加评奖,会影响官员的政绩?”“是不是他们动员我入党,我因为怕开会没答应?” 我说:“都不是。主要是你创建东方音乐剧的大踏步实践,严重超越了这里的文化管理体制。正好,又遇到了我的事情。全国那么多人在报纸上对我的长时间围攻,给他们造成一个深刻的印象。” 妻子没有反驳。 那年,她才38岁,和当年严凤英离开人世是同样的年龄。所不同的是,马兰已经把自己所在的剧种,推到了当代国际戏剧学的大门口,只差了几步。 上海没法留了,安徽不让留了,我们能到哪里去呢? 马兰最看不得的是她的爸爸、妈妈也受到波及。就在前不久,当马兰带着剧团到海内外演出让大家都风光无限的时候,她的爸爸、妈妈几乎天天都看到人们热情的笑脸。现在,大多数人的笑脸都冰冻了。两位老人家又回到了做“右派”的年月,面对着一双双冷眼。 三里街的住所看不到旭日,却能看到一小角夕阳。马兰背靠着几件徽派的木雕看着我,久久不说话。 她平日几乎不流泪,这次却流泪了。她赶忙擦去,别过身去看夕阳。 这个夕阳下的剪影,让我连续几天都失眠。 (摘自《吾家小史》 作者 余秋雨) |
|
≡ 洛阳社区最新图片 ≡ | ≡ 洛阳社区热帖 ≡ | ||
≡ 房产家居 ≡≡ 汽车时代 ≡ | ≡ 河洛文苑 ≡≡ 馋猫大本营 ≡ | ≡ 聚焦河洛 ≡≡ 亲子教育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