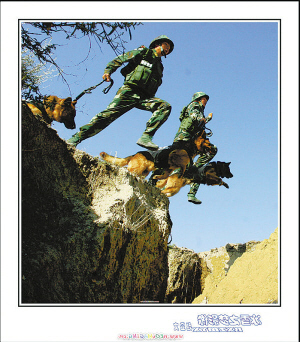|
||||||||||||||
 |
|
|
2012 年 5 月 22 日 星期 二 |
|
||
| 夕花朝拾>>> |
| 战 友 |
| □如水 |
午夜,突然接到南疆边防某部教导员杨猛的电话。他说,他和几个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老兵在喝酒,喝得掉眼泪,忽然就想到我。 杨猛所在部队驻防在战事贯穿于20世纪80年代的老山前线,直到今天,那片红土地依然被数十万老兵所牵挂,每年都有大量参战老兵重访老山。不少老兵在重回老山时与杨猛成了忘年交,我算其一。 放下杨猛的电话,我被“战友”折磨得彻夜难眠。 战友是什么?“相见亦无事,不来忽忆君”,战友是那忽然忆起的人? 去年夏天的一个午夜,我睡得正香,被省城一位厅长的来电惊醒。他来洛阳视察工作,晚上喝多了,兴奋,夜半想到我这个战友,就对着手机把无处诉说的牢骚和为官的无奈说给我听。说到动情处,他的声音竟有些异样。我不插话,静静地听,一直听了40多分钟。 他说,那些话只能跟我这个战友说,连老婆都不说。我在电话这端不由自主地频频点头。我很感动,在这漆黑的午夜,我的心是对战友敞开的窗。 我劝他少喝点儿酒,他说,没办法,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战友相聚,远离江湖,喝酒反而更厉害。不是“没办法”,而是自己要喝,劝不住。 记得一次战友聚会,一名偏瘫的战友,在妻子搀扶下租车赶了一百多里路到场。席间,这位本不该喝酒的战友喝得最多,劝也劝不住。他汪着泪眼说,其他时候不喝酒,与这些战场上幸存下来的战友们聚在一起,一定要喝! 几分豪放,几分悲壮,让人想起临上战场时喝酒壮行的情景。 还有一次战友聚餐,把陈酿喝出了苦涩,喝出了血腥的凝重。 一个我不认识的老兵,患肝癌,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便向医生提出要求,让医生给他安排一次聚餐,他要与战友们最后喝一次酒。曾当过兵的我被叫去作陪。老兵让他侄子站在身旁替他喝,他举着酒杯说了一大堆感谢战友满足他最后愿望的话后,就因体力不支回病房了。 几天后,老兵走了。在他人生尽头喝的那次酒,让我想起了“最后的晚餐”。我们朝着他的方向举着酒杯,分明听见他说,喝吧,这杯里流着我的血,喝了它,为的是念着战友! 这世间,许多简单的事,与“战友”挂上,就变得沉重、复杂,剪不断,理还乱。 在老山前线时,我到硬骨头六连调研,与某部副指导员谢关友一起拍照,由于懈怠,照片还没有送给他,他就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这让我悔青了肠子,我把这件事写在参战日记里,写在散文里。20多年过去了,懊悔抹不去。那张照片我不忍看,却一直珍藏着。 看过我文章的战友给我讲谢楠,一个老山女兵的故事。“战友”让她纠结,甚至改变了她的生活轨迹。 在老山作战时,谢楠在野战医院当卫生员,天天与血肉模糊的伤员打交道。有个伤员被截了四肢,只一个躯体搁在床上,心情不用说有多坏,怄气,不吃饭。谢楠喂他,他让谢楠唱歌,唱一句吃一口。谢楠就唱,边唱边喂,那伤员眼泪哗哗流,谢楠跑到墙角号啕大哭。 谢楠的同乡赵勇想买一个录音机,差15块钱,就利用往医院送伤员的机会向谢楠借。谢楠身上只有15块钱,就留了5块钱自己用,借给赵勇10块钱。因为差5块钱,赵勇没有买成录音机,又去了前线,却再也没有回来。 赵勇牺牲后,谢楠看到5块钱就难受,心里有一种痛。5块钱把一个牺牲的战友和谢楠永远地系在了一起。 又有战友牺牲了,谢楠跑到麻栗坡烈士陵园为战友送行。那时战事吃紧,烈士不断地增加,新来的烈士还没有写出名字,谢楠找不到战友,悲愤地举起冲锋枪,对天扫射…… 听到这里,我心头一热:好一个谢楠,你该叫“血男”呀,一个豪情万丈的血性男儿。 最终,谢楠因“违纪”丢了战功,脱下了军装。 脱了军装的谢楠上了大学,在北京中关村办起自己的公司,生意做到国外。 然而,闲暇时谢楠总被“战友”牵挂着,煎熬着。下雨时她会想到那个没有了四肢的伤员:伤口疼不疼,谁照顾他,成家没有……夜里老做梦,梦见浑身泥水和血水的战友赵勇。 谢楠心里痛,她要去看战友,了却一桩心愿。 于是,在离开战场19年后的一个午夜,谢楠来到了曾发誓不会再来的麻栗坡,只身走进了烈士陵园。在那安睡着957个英灵的山坡上,谢楠借助打火机的亮光找到了赵勇的墓,为这个同乡烧了一张5元钱。 这一年,谢楠从中关村辞职,举家迁到昆明,只为离战友近些。此后,她年年都去烈士陵园祭扫。她说她感觉有某种召唤。 那召唤是什么?当然是“战友”!想起一首歌的歌词:战友是两双紧握的手,战友是一杯浓浓的酒,战友是一口大锅舀出的兄弟情,战友是一身军装打扮的亲骨肉,危难时才显情深义厚,分手时才觉得最难分手。 听完谢楠的故事,一缕淡淡的牵挂和思念从我的心底慢慢溢出,郁郁而悠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