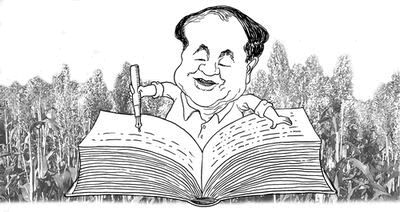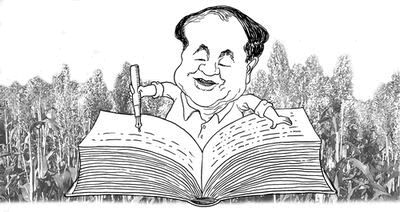 | | (资料图片) |
|
《红高粱家族》是我创作的九部长篇中的一部,但它绝对是我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因为迄今为止,很多人在提到莫言的时候,往往代之以“《红高粱》的作者”。这部小说的第一部《红高粱》完成于1984年的冬天,当时是作为中篇写的,也是作为中篇发的。最初的灵感产生带有一些偶然性。那是在一次文学创作讨论会上,一些老作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有二十八年都是在战争中度过的。老一辈作家亲身经历过战争,拥有很多素材,但他们已经没有精力创作了,因为他们最好的青春年华被耽搁在“文革”当中。而年青一代有精力却没有亲身体验,那么他们该怎样通过文学来更好地反映战争、反映历史呢?
当时我就站起来说:“我们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弥补这个缺陷。没有听过放枪放炮但我听过放鞭炮;没有见过杀人但我见过杀猪甚至亲手杀过鸡;没有亲身跟鬼子拼过刺刀但我在电影里见过。因为小说家的创作不是要复制历史,那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小说家写战争——人类历史进程中这一愚昧现象,他所要表现的是战争对人灵魂的扭曲或者人性在战争中的变异。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也可以写战争。”
我发言以后,当场就有人嗤之以鼻。事后更有人说我狂妄无知,说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说我是“碟子里扎猛子——不知深浅”。在我的创作生涯中,有好几次我都把自己逼到悬崖边。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我必须马上动笔,写一部战争小说。我在落笔之前,很是费了一番斟酌。我发现“文革”前大量的小说实际上都是写战争的,但当时的小说追求的是再现战争过程。而我认为,战争无非是作家写作时借用的一个环境,利用这个环境来表现人在特定条件下感情所发生的变化。这样的观念、这样的写法今天看来比较合乎文学创作规律,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经历了长期“左”的思想禁锢后,还是被很多人质疑和不能接受的。
有了这样一个出发点,我开始构思,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家乡。我小时候,人口稀少,土地广袤,每到秋天,一出村庄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缘的高粱地。在“我爷爷”和“我奶奶”那个时代,人口更少,高粱更多,许多高粱秆冬天也不收割,这为绿林好汉们提供了屏障。于是我决定把高粱地作为舞台,把抗日的故事和爱情的故事放到这里上演。后来很多评论家认为,在我的小说里,红高粱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植物,而且具有某种象征意义,象征了民族精神。确定了这个框架后,我只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部在新时期文坛产生过影响的作品的初稿。
《红高粱》源自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我所住村庄的邻村。先是游击队在胶莱河桥头打了一场伏击战,消灭了日本鬼子一个小队,烧毁了一辆军车,这在当时可是了不起的胜利。过了几天,日本鬼子大队人马回来报复,游击队早就撤得没有踪影,鬼子就把那个村庄的老百姓杀了一百多口,村子里的房屋全部被烧毁。
《红高粱》塑造了“我奶奶”这个丰满鲜活的女性形象,并成就了电影《红高粱》中的扮演者巩俐。但我在现实生活中并不了解女性,我描写的是自己想象中的女性。在20世纪30年代农村的现实生活中,像我小说里所描写的女性可能很少,“我奶奶”也是个幻想中的人物。我小说中的女性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女性是有区别的,虽然她们吃苦耐劳的品格是一致的,但那种浪漫精神是独特的。
我一向认为,好的作家必须具有独创性,好的小说当然也要有独创性。《红高粱》这部作品之所以引起轰动,其原因就在于它有那么一点独创性。将近三十年过去后,我对《红高粱》仍然比较满意的地方是小说的叙述视角,过去的小说里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而《红高粱》一开头就是“我奶奶”、“我爷爷”,既是第一人称视角又是全知的视角。写到“我”的时候是第一人称,一写到“我奶奶”,就站到了“我奶奶”的角度,她的内心世界可以很直接地表现出来,叙述起来非常方便。这就比简单的第一人称视角要丰富得多开阔得多,在当时也许是一个创新。
有人认为我创作《红高粱家族》系列作品受到了马尔克斯的影响,这是想当然的猜测。因为马尔克斯的作品《百年孤独》的汉译本1985年春天我才看到,而《红高粱》完成于1984年的冬天,我在写到《红高粱家族》的第三部《狗道》时读了这部了不起的书。不过,我感到很遗憾——为什么没有早想到用这样的方式来创作呢?假如我在动笔之前看到了马尔克斯的作品,估计《红高粱家族》很可能是另外的样子。
我认为,像我这种年纪的作家毫无疑问都受到了西方文学的影响,因为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是封闭的,西方文学发生了哪些变化,有哪些作家出现,出现了哪些了不起的作品,我们是不知道的。改革开放以后,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被翻译过来,我们有一个两三年的疯狂阅读时期,这种影响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从而不知不觉地就把某个作家的创作方式转移到自己的作品中来了。
为什么这样一部写历史写战争的小说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响,我认为这部作品恰好表达了当时中国人一种共同的心态,在长时间的个人自由受到压抑之后,《红高粱》张扬了个性解放的精神——敢说、敢想、敢做。但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创作的社会意义,也没有想到老百姓会需要这样一种东西。如果现在写一篇《红高粱》,哪怕你写得再“野”几倍,也不会有什么反响。现在的读者,还有什么没有读过?所以,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一样,每部作品也都有自己的命运。 (摘自《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