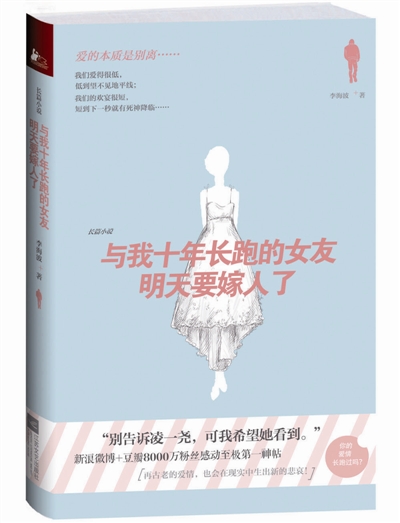|
||||||||||||||
 |
|
|
2013 年 11 月 4 日 星期 一 |
|
||
| 爱情长跑 催人泪下 |
| 14 重返南京 |
他毫不客气地说:“混凝土凝固了,那就把它凿开。” 协商数次无果,施工单位终于恼了,平时称兄道弟的人拦住监理,将弱不禁风的老头子按在黄沙堆里揍了一顿。最后,他们还丢下一句话:“你们这种垃圾货色,给脸不要脸,欠揍的玩意儿,老子看在你们是业主走狗的分上才丢点骨头给你们,你们还真蹬鼻子上脸了?” 老监理其实没有受伤,但他是一个爱面子的人,这次如此狼狈不堪,心理创伤一时无法弥合。他被打的事情被当作笑话到处传播,甚至我在场的时候,工人们也毫不避嫌,仍添油加醋地描述。 我只是一个资料员,很少去做得罪人的事情,他们没有为难我,但我仍然被伤到了,我想这辈子决不做一个捡食别人残羹剩饭的走狗。 原因之二是凌一尧本科毕业后,考取了本校的研究生。 在这个时候,我想再过几年就该谈婚论嫁了,因而我的紧迫感变得强烈了,希望能在她毕业前多赚一些钱,至少能圆她一个“白婚纱、红地毯、鲜花拱门”的梦想。 于是,我重返南京,和凌一尧三年的同居生活正式开始了。 我在江宁区找工作,采用全面撒网的战术,简历一下子投出去十几份,然后逐个单位去面试,忐忑不安地等候消息。我寻找的工作类别相当广泛,有企业行政、广告策划、网站编辑、经理助理,甚至保险公司的业务销售等。 最终,我被一家广告公司录用,成为一名朝九晚五的办公室文员。 我们住的房子是凌一尧跑了很久才找到的,不到40平方米,月租600元。房子的位置有些偏僻,位于半个世纪前的老街区。房东的院子里有一口老井,井沿竟然刻着“镇江”的字样,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半个世纪以来,脚下这片土地的管辖权在镇江与南京之间数次变换。 周末我们一起去附近的小商品批发市场,购置了许多生活用品。房子里原本就有床铺和电视机,再添上折叠衣橱、被褥、晾衣架、炊具和餐具,原本满是尘土蛛丝的房间顿时变得生机盎然。 “我们有小窝了!”凌一尧眉飞色舞。 我也高兴地将她抱了起来。 在我和凌一尧恋爱的第五个年头,我们第一次朝夕相处于同一屋檐下。 经过友好协商,我们达成共识:我负责炒菜,凌一尧负责洗碗。饭后,我惬意地躺在床上看电视,而她不停地忙碌着,挽着袖子,系着围裙,像个妻子一样做着家务。 当时我还在试用期,收入少得可怜,要承担房租水电以及其他开销,生活有些窘迫,不得不尽量节省着过日子。譬如我们的早餐,经常是一小锅米粥、一小碟肉松榨菜、两个煮鸡蛋。 我们约定,谁先起床谁先去做早餐,但每次当我醒来时,早餐都已经摆在桌上了。我百思不得其解,凌一尧根本不是一个容易自然醒的人,可是我又从来听不到闹铃声。后来我才明白,她把手机闹铃调成震动模式,放在她的枕头边,这样她便可以早起做饭又不会把我吵醒。 “白痴,手机会有辐射的啊!”我埋怨道。 她说:“我就是喜欢喊你起床吃早餐呀!” 她那得瑟的模样,就像幼儿园里得了小红花等待表扬的小朋友,而我突然觉得不可思议:我得有多幸运,才会得到这个女孩的青睐! 为了节省费用,方便出行,我从附近大学城的毕业生手里买了一辆山地车,花了120块钱。每天早晨,我骑车上班时载她一程,傍晚再去她学校北门,载她一起回家。两个时间段都是交通拥堵的高峰期,汽车司机们焦躁地按着喇叭,而我们的山地车灵活地穿行在路上,畅通无阻。 “报告首长!前面有一辆宝马,是否超车?” “超!” “是!” 于是,一辆辆宝马、奔驰甚至兰博基尼,被我们驾驶的环保节能无噪声的“单兵无履带战车”甩得远远的。 (摘自《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 李海波 著) |
|
≡ 洛阳社区最新图片 ≡ | ≡ 洛阳社区热帖 ≡ | ||
≡ 房产家居 ≡≡ 汽车时代 ≡ | ≡ 河洛文苑 ≡≡ 馋猫大本营 ≡ | ≡ 聚焦河洛 ≡≡ 亲子教育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