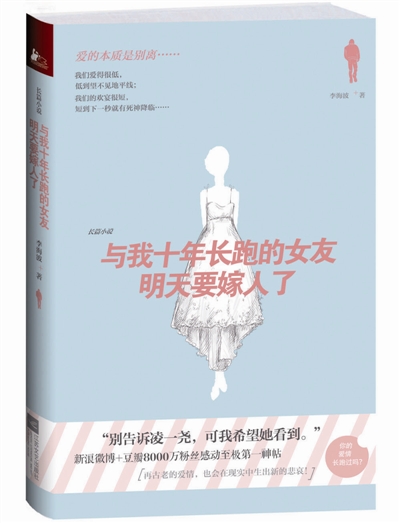|
||||||||||||||
 |
|
|
2013 年 11 月 8 日 星期 五 |
|
||
| 爱情长跑 催人泪下 |
| 18 女友说谎 |
我有些受挫,垂头丧气地跟她一起回家,不料关门以后,她一边埋怨我乱花钱,一边把花夺过去闻了又闻,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她在阳台上翻了半天,终于找到一个透明的玻璃瓶,装上清水,将玫瑰养在里面。 “浪费钞票,我还得伺候……”她仍然喋喋不休地说着。 “那你为什么早上看别人送花表白那么激动?” “喜欢看戏又不等于喜欢演戏,再说在大街上被人围观是很难为情的,像个白痴一样。” 我问道:“那举办婚礼的时候怎么办?那么多人围观……” 凌一尧想了想,居然露出紧张的神色:“是啊,还真是一道坎儿,好可怕,我现在就得开始作心理准备了。” 于是,她真的准备起来,譬如在打电话叫我去接她时,叫我带一点儿蒙古烤肉或者关东煮,见面交给她要含情脉脉,柔情似水,就像情人节送玫瑰一样浪漫。当我双手将食物奉上,她郑重其事地接过去,说:“哇,好香呀!” 那情景与情侣送花别无二致。 一天,她坐在椅子上,悠闲地荡着小腿,将我买的食物吃得干干净净的,我拿着纸巾和矿泉水在旁边伺候着。她喝了一口水,抬头望着外面的天空,然后掏出手机,说:“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合一张影吧。” 她挎着我的胳膊,另一只手平举手机刚要拍摄,手机就响了起来,她看了一眼,顿时紧张起来,一边往旁边走,一边低声嘱咐我:“我妈打来的,你别出声。” 原先温馨的气氛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相恋多年,她经常说这句话。在年少时,我们像两个贪玩的孩子一样,喜欢偷偷摸摸地经营这种隐秘的地下恋情,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那分窃喜渐渐远去,取而代之的是日益弥漫却又无法说出口的压力。 我们这拨青年通常会遭遇一个滑稽的现象,在十七八岁时,父母对我们的个人感情风声鹤唳,无时无刻不在严防死守,仿佛恋爱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丑事。但儿女到了二十三四岁时,他们又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对下一代婚恋的监察。 以我为例,高中因早恋而遭到校方处分的事情对于我爸妈而言是一个莫大的耻辱,每当我给同学打电话时,我妈都会一言不发地从旁边走过,在吃饭时才问:“刚才你在房间里给谁打电话呢?” 上大学以后,倘若我在家给别人打电话,我妈又会借倒茶或者找东西的名义在旁边晃悠,然后满怀期待地问:“谁啊?男的女的?” 这个现象在凌一尧家显得尤为极端,她爸妈明令禁止她在大学毕业之前谈恋爱,他们说:“不要把青春浪费在那些不懂事的男孩子身上。”幸好,我们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周围的朋友也帮忙打掩护,放假的每次约会都由某个女生扮演崔莺莺的角色,把她从家里带出来交给我。 “你们结婚时我要当伴娘。”不止一个“崔莺莺”这样讲。 凌一尧读研后,她爸妈经常旁敲侧击地问她有没有谈恋爱。她怕父母反对,习惯性地隐瞒,直到研究生二年级,她爸妈要给她介绍对象,她才慌乱起来。 “我已经谈恋爱了。”她小心翼翼地说。 她妈妈在电话那头问:“什么时候谈的?” 凌一尧瞅了我一眼,说:“大半年了。” “什么?为什么这么久了都不告诉我?”她妈妈的声音陡然提高,似乎恨不得立即从电话里冲出来,拎着她的耳朵,敲她的头。但她又缓和下来问:“他多大?哪里的?怎么认识的?” “也是如皋的,以前高中时的同学。” “噢。”她妈妈又问,“他也在读研究生吗?” “不是,他大学毕业就工作了。” 我压低声音问:“要我和她讲话吗?” 凌一尧捂住手机,小声说:“不用,你先做饭吧。” 她显然有些不自在,下意识地背对着我,话筒里的声音变得模糊了。我知趣地起身去做饭,依然竖起耳朵留意着,虽然不知道她妈妈问了什么,却依稀听见凌一尧的只言片语:“他……在广告公司工作……刚升了部门经理……挺不错的,一个月工资大概8000元……” 我心不在焉地打着鸡蛋,情绪非常低落。 在晚餐时,我们默不作声地吃饭,气氛有些尴尬,连一声咳嗽都显得突兀。最终,我忍不住开口问道:“你为什么要对你妈说谎?” (摘自《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 李海波 著) |
|
≡ 洛阳社区最新图片 ≡ | ≡ 洛阳社区热帖 ≡ | ||
≡ 房产家居 ≡≡ 汽车时代 ≡ | ≡ 河洛文苑 ≡≡ 馋猫大本营 ≡ | ≡ 聚焦河洛 ≡≡ 亲子教育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