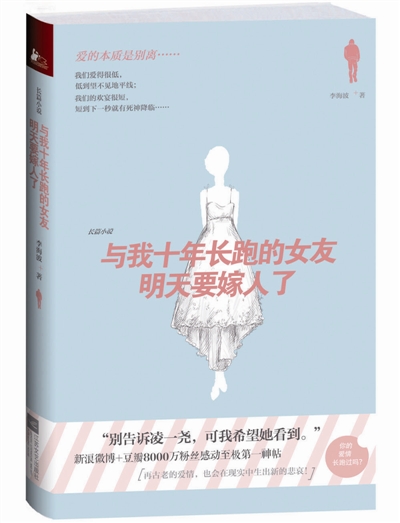|
||||||||||||||
 |
|
|
2013 年 11 月 11 日 星期 一 |
|
||
| 爱情长跑 催人泪下 |
| 19 与女友吵架 |
“我不是说这个。”我打断她的话。 凌一尧抬头看了我一眼,又迅速低下头去,若无其事地说:“那你让我说什么?” “我只是一个小职员,月薪3500元,你为什么说我是月薪8000元的部门经理?难道我现在的状况很丢人,让你觉得没有面子?” 她说:“现在先稳住我爸妈再说,反正暂时又不见面,时间还很多。说不定等到那一天,你已经达到这个水平了。” “万一达不到呢?” 她想了想,说:“那我就说你突然被降职了……” 我憋了一晚上的坏情绪,一时半会儿无法消除,仍然带着一腔火药味地问:“部门经理,月薪8000元,是你家择婿的最低标准吗?你爸妈是不是很在乎这些?” 凌一尧也生气了,反唇相讥道:“在乎了又怎么样?难道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顿时有种尊严遭到践踏的屈辱感,认为她瞧不起我,于是甩下碗筷,自个儿生起闷气。凌一尧当时正在为课题和工作的事情发愁,压力很大,她无法承受我发起的冷战,平生第一次与我吵开了。 她说:“你要是有一点长进,我何必编那些瞎话?当初你说早点参加工作攒钱娶我,可是你现在除了一文不值的自尊,还有什么拿得出手?” “我怎么就没长进了,我从毕业到现在,哪一天不在认真工作?我烟酒不沾,不赌不嫖,工资都交给你了,还要怎么样?”我一时控制不住情绪,越说越气愤,“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你又不是第一天知道我没钱没出息,如果你嫌弃我,现在可以去找个小老板,不用跟着我受穷。” 话一出口,两个人瞬间都沉默了。 她气得躲在小阳台抹眼泪,而我独自待在房间里,固执地认为自己才委屈呢。但再环顾一圈,看到她那个很久未换的旧包,那个空空如也的梳妆台,还有那只我送给她的,使用两年依然洁净如新的手机,突然心痛起来。 我走到阳台上,将她拥入怀中,说:“对不起。” 她没有顺从,也没有抗拒,只是望着城市的一隅,目光里满是迷茫。我渐渐地意识到,现在已经不是无忧无虑的高中,也不是快乐与多梦的大学,我若化不开她对未来的忧虑,兴许会永远失去她。 在这个光怪陆离的城市里,有人出卖青春、肉体与灵魂,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也有人勤奋隐忍,如履薄冰,却连小小的幸福都难以维持。 那年初夏,我再也无法在广告公司的小隔间里安坐,一有闲暇时间便登录各大求职网站,希望能够寻觅到一个更好的工作。我揣着理工科的文凭,有心从事文科的工作,因此投出去的求职书大都石沉大海,只有一家制作网页游戏的公司给出了文案的职位。 那个职位月薪4000元,交三险一金,又是文字工作,与我的期待颇为相符。 恰在此时,很久以前那个与我探讨人生的项目经理老刘找上门来。老刘比我大8岁,很早便出来闯荡,如今自己拉起工程队单干。他说:“小吕,记得你以前在测量和预算方面比较在行,我在南通这边做围海工程,刚好缺这方面的技术员,你愿不愿意过来一起干?” 我说:“不好意思,哥,我在南京工作,不在南通。” “那你认识这方面的人吗?帮忙介绍介绍。” “我的同学里倒是有,我给你去找找,不过你那边具体是做什么工程,大概提供怎样的薪酬,你说说,别人问起来我也好有一个答复。” “看具体能力,能力一般就4000元,能力很强的可以开到8000元。” 我又问:“那怎样算一般?怎样算能力强?” 他想了想,说:“这样讲吧,如果你来的话,我给你6000元,你可以用这个标准去判断。” 一方面,我着手在电话簿、QQ和校友录里帮他找人;另一方面,我又不是那么尽心尽力。因为,在物价尚未飞涨的当时,他所给的待遇对我是一个极大的诱惑。 “有没有找到人呀?”他几次催促。 “还没有,他们有的有项目暂时走不开,有的嫌在海边干太苦,不愿意去。” (摘自《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 李海波 著) |
|
≡ 洛阳社区最新图片 ≡ | ≡ 洛阳社区热帖 ≡ | ||
≡ 房产家居 ≡≡ 汽车时代 ≡ | ≡ 河洛文苑 ≡≡ 馋猫大本营 ≡ | ≡ 聚焦河洛 ≡≡ 亲子教育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