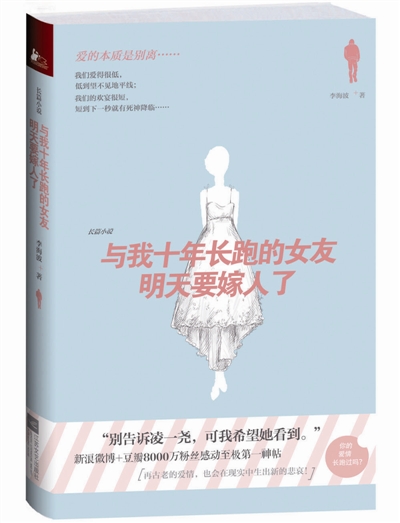|
||||||||||||||
 |
|
|
2013 年 11 月 12 日 星期 二 |
|
||
| 爱情长跑 催人泪下 |
| 20 跳槽做监理 |
闯,对于我那朝九晚五、一成不变的生活而言,就像一枚石子投入宁静的湖面,发出悦耳的声响,也荡开一层又一层涟漪。 我有些心动,但还是踌躇不决。 “考虑一下,咱老爷们儿就该出来闯荡天下,多见见世面,不要窝在温室里过小日子。你到这边来,哥绝对不会亏待你,这个项目相当不错,光是土方量就非常可观,而且这是市政工程,付款方式也挺靠谱。” 当人到山穷水尽又遇柳暗花明之时,便会轻易皈依命运之说,而此时我尤为相信这是上天赐予我的千载难逢的翻身机会。 于是,我一口答应下来。 在监理公司的那一年,我对工程方面的工作颇为厌倦,但现在我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我要闯出一片天地,要赚取足以让我安身立命的资本,向凌一尧证明我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窝囊废。 当我愉快地将这件事情告知凌一尧时,她却非常生气,拿起枕头便砸了过来,责问道:“谁让你答应下来的,为什么不事先和我商量一下?” “有什么好商量的?这样的机会可不是大街上随便就能捡来的,就算南京的大街上可以捡,我下手不快也会被别人捷足先登。” “那你就把我一个人丢在南京?” 我顿时觉得她不可理喻,反驳道:“那你要怎么样?又嫌我没出息,又嫌我走得远,我总不能在家骑着竹马给你建功立业吧?” 凌一尧欲言又止,最后还是没有开口。我知道,我伤到她了。 她明白我意已决,再也没有作过多的阻拦,默默地给我收拾行李,而后与我一起站在马路旁边,等候前往海边的长途汽车。 我总觉得时间还早,临走时再告别一下也无妨,但客车突然出现,售票员不等车停稳便探出脑袋大喊:“快点上来!巡逻车来了就要罚款了!” 我赶紧拎着行李箱跳上客车,来不及给凌一尧一个拥抱。当客车再次开动时,她站在卷起的尘土里,头发在风中飘动,抬手向我轻轻一挥,我整颗心猛地沉了下去。 我得有多大的决心,才会踏上一条离她越来越远的路呀? 每当我喝醉了酒感到天旋地转时,我的脑海中都会浮现无数个凌一尧的身影。那个穿着校服,扎着马尾辫,清秀又稚气的凌一尧;那个在昏暗路灯下偷偷塞字条给我的凌一尧;那个一接吻就会忍不住闭上双眼的凌一尧;那个睡到半夜突然抱住我的胳膊说“我爱你”的凌一尧。 但唯有那个站在黄昏余晖中无奈地目送我远去的凌一尧,最让我寝食不安,甚至哪天让我死不瞑目。 我要去的不是海滨度假胜地,而是位于黄海滩头的工地,条件非常艰苦,苦不堪言。 这里的气候非常恶劣,紫外线强度高,海风像刀子一样,脚下的土地看似坚实,但踩上10秒钟就能踩出一个吃人的陷阱。我们住在活动板房里,而工人们直接搭了简易窝棚,外面的风雨敲大鼓,里面的风雨唱小调。除此之外,饮水也是很大的问题,钻井打出来的都是黄褐色的咸水,无法饮用,只能从十几公里之外的小镇运水。 我入职的第一天,快乐的海鸟便向我展示它独特的欢迎方式——当我信步走在滩地上时,几只海鸟在我的头顶上方不停地盘旋怪叫,那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情景太让人感动了,我一度将自己想象成在草原上扬鞭策马,身后鹰雕翱翔的郭靖。 可惜,那几只海鸟突然神经质地俯冲下来,对我发动车轮战,在快要啄到我头顶时又怪叫着飞了上去。我正要破口大骂,一团湿漉漉的东西落下来,不偏不倚地砸在我的肩膀上,原来那是白花花的鸟粪。 我打电话将这些事说给凌一尧听,但她还在生我的气,幸灾乐祸地说:“你就知足吧,那鸟本来要把粪便丢进你嘴里的,可惜技艺不精丢偏了,下次你可没这么好运。” “我又没惹它们!” “可你惹我了!它们就是我的怨念变成的精卫鸟,专门去海边教训你的。” (摘自《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 李海波 著) |
|
≡ 洛阳社区最新图片 ≡ | ≡ 洛阳社区热帖 ≡ | ||
≡ 房产家居 ≡≡ 汽车时代 ≡ | ≡ 河洛文苑 ≡≡ 馋猫大本营 ≡ | ≡ 聚焦河洛 ≡≡ 亲子教育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