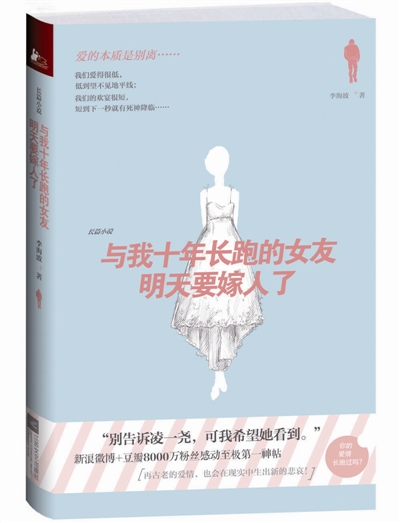|
||||||||||||||
 |
|
|
2013 年 11 月 18 日 星期 一 |
|
||
| 爱情长跑 催人泪下 |
| 24 小孟救急 |
我疑惑地问:“老冯的侄子不就是驾驶员吗?” “他侄子来了,还会留路给你走?”他白了我一眼。 “那我也找不到人啊。”我摊手表示无奈,“我自己倒是能够鼓捣几下子,但只能挖个坑埋个土,不太专业。” “那你先客串驾驶员,辅助做一些简单的事情,三天内要是找不到别的驾驶员,只能让老冯的侄子过来了,到时候你可别抱怨。” 老刘在外面闯荡多年,不可能找不来一个挖掘机驾驶员,但他将这个任务交给我,显然别有意图。我四处打听却毫无着落,刚好子石打电话过来闲扯。他说他已经恋爱大半年了,对方叫汪小菲,是南通市人。他们爱得缠缠绵绵,两人已经以“老公”和“老婆”互称了。 “吕总在海边混得怎么样?”他问我。 我的心情有些郁闷,随口提及工作上的烦心事,他说:“小孟这两年不是一直在学这个吗?” “哪个小孟?” “你高中时的小弟啊,帮你和凌一尧传字条的那个人。” 我赶紧要了小孟的电话号码打了过去,尽管失去联系很久,小孟还是很快听出我的声音。他这人还是性子直,前段时间,他把自己所在公司老板的小舅子揍了一顿就跑了,现在是一个赋闲在家的无业青年。叙旧片刻,我就提到正事,小孟激动地毛遂自荐:“哥,你找对人了!什么挖掘机、推土机、装载机我都会,还是一把好手;叉车、吊车、翻斗车也懂点儿,绝对不会给你丢面子!” “那你打算要多少工资?” 他不假思索地说:“这个好说,哥觉得多少合适,那我就拿多少!” 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我当然不可能压他的工资,于是向老刘报告了这件事,最终老刘开出了每月5000元的工资。第三天,小孟便背着被褥出现在工地上,只见他戴着蛤蟆镜,嘴里叼着烟,脖子上挂着双节棍。他希望自己的首次亮相耀眼一点,但是工地上的那只哈士奇狗丝毫不怕他,龇牙咧嘴地追着他吼了大半天。 在他铺床的时候,它在吼;在他吃饭的时候,它在吼;在他午休的时候,它在吼;在他逛工地的时候,它在吼;就连他去厕所时,那条狗仍然锲而不舍地在他旁边狂吠。 “哥啊,你们这只狗是不是有神经病?”他打电话过来告状,“我都蹲半个小时了,连一个屁都没放得出来!谁养的?他怎么不弄一只兔子看工地?” 事实上,这只哈士奇是老刘从朋友家牵来的,当时他认为这只狗的目光凶狠霸气,带到这里必有用武之地。然而,它到工地以后不务正业,好逸恶劳,整天在海边瞎溜达,不但看不了工地,我们还担心它被人偷走。 原先,老刘认为小孟可能是继哈士奇之后第二个错招的劳动力,我也曾有所担忧。第二天,小孟在众目睽睽之下驾驶挖掘机干活,任务看似普通却需要细腻的操作,很多人等着看笑话。然而,他的技术相当娴熟,任务完成得又快又好,连一向吹毛求疵的老刘都表示赞许。 “有了这个小兄弟,那俩老驾驶员摆不了谱了。”老刘欣慰地说。 老刘是项目部的经理,老冯是总工,而我的职务不过是小小的技术员。尽管如此,每次项目部在镇上吃喝宴请老刘都会把我带上,因为一场酒席就是一场战斗,我在这场战斗中充当老刘的贴身警卫员。倒酒、分酒、敬酒、劝酒、罚酒、灌酒,这些都是在学校学不来的,但可能比高等数学有用。 这一喝便是一顿接一顿,有时上顿的酒还没醒,下一顿的酒又开始了。 那天为了报价的事情我们又请客,在觥筹交错的时候,凌一尧突然打来电话,我赶紧走出包间接听。她的声音有些颤抖,低声地说:“我肚子疼得厉害。” “怎么了,是不是着凉了?”我问。 “疼得都不想动,晚饭都没有吃。” “会不会是急性肠炎或阑尾炎?蒋倩倩不是在南京吗,要不我打电话给她,拜托她送你去医院看一下?” “哦,知道了。”她话锋一转,“那你在干什么?” 我如实相告:“在外面喝酒。” 凌一尧无奈地苦笑:“那你继续喝吧。” “只是应酬,我也不想喝,回去后我再给你打电话……” (摘自《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 李海波 著) |
|
≡ 洛阳社区最新图片 ≡ | ≡ 洛阳社区热帖 ≡ | ||
≡ 房产家居 ≡≡ 汽车时代 ≡ | ≡ 河洛文苑 ≡≡ 馋猫大本营 ≡ | ≡ 聚焦河洛 ≡≡ 亲子教育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