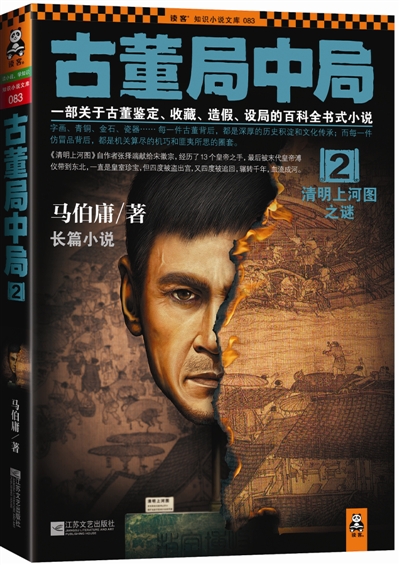|
||||||||||||||
 |
|
|
2013 年 11 月 28 日 星期 四 |
|
||
| 机关算尽 匪夷所思 |
| 35 我被质问 |
“惨败。”药不然一摊手,脸上的笑意全没了。 “我看,老老实实跟人家姑娘说得了,不要搞歪门邪道。” “要说你去说。”药不然眼皮一翻。 我略作思索,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戴海燕面前。戴海燕把手里的书放下对着我笑,就是不说话。 我毕恭毕敬地问:“是戴老师吗?” “你早就知道了,何必多问这么一句废话?”戴海燕虽是娃娃脸,嘴巴却尖刻得很。我这才意识到,那笑意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怜悯,大概就像是周瑜看见来盗书的蒋干时浮现出的笑意吧。 她这么一说,我顿时有点接不下去了,脑子里转了一圈,我决定还是说实话。我坐到她对面,语气平淡:“您好,我有一些关于《清明上河图》的问题想请教一下。我们来自北京,我叫许愿,是中华鉴古研究学会的。”我作了自我介绍。 戴海燕的表情有点意外:“你是许愿?” “你知道?” “最近报纸上都是《清明上河图》的报道,你现在可是个红人。”她看了看墙上的石英钟,站起身来,“时间快到了,我要去上课,你们想知道什么晚饭后到我宿舍来。我之所以答应跟你谈话,只是想借这个机会当面告诉你,你有多么愚蠢。” 戴海燕把目瞪口呆的我抛在原地,她起身离开图书馆。药不然凑过来问进展如何,我说咱们晚上去她宿舍详谈。药不然一伸大拇指:“哥们儿,你果然深藏不露,已经有我在大学时的八成风采了。” 我苦笑着摇摇头,不知该怎么描述自己的感受,心想,这个女人不简单,绝对不简单。 到了晚上快7点时,我和药不然悄悄走进博士楼,来到戴海燕的房间。 戴海燕拿起《首都晚报》抖了抖说:“我要说的,就是你这篇荒唐的报道。我这个人有洁癖,不能容忍那些愚蠢的和错误的东西。” “愿闻其详。”我简单地说。 戴海燕把报纸打开,说:“你在这里讲了一个传奇故事。在你的故事里,陆夫人的王姓外甥在陆府观画,不带纸笔,只凭记忆,前后数月终于绘出一幅赝品,这一开始就大错特错!你以为古人临画真是靠记忆吗?临画和抄书是两码事。抄书是记录符号,只要内容对了,笔迹形式并不重要,但临画完全不一样,运笔形式就是内容本身,这是一种技巧性的工作,哪怕对照着画,都很难做到一模一样,别说死记硬背了,像《清明上河图》这种细节无比庞杂的画,更不可能靠死记硬背去复制。” “也许人家是天才。”我说。 “也许?但我相信另外一种解释,你是个笨蛋。”戴海燕毫不客气地继续说,“你小时玩过蜡烛吧?蜡烛的烛油滴到纸上,会让纸张变得透明。古人临画,也是同样原理,他们先在宣纸上涂黄蜡,用灌满热水的铁斗压在上面反复碾压,让蜡彻底融入纸面,使纸变得透明。然后临摹的人会把透明纸铺在原画之上,用细笔在透明纸上描出线条,再拿开对着原画临摹。临摹一幅画都如此费劲,你讲的故事里那个王姓外甥想靠记忆复制一幅名画,根本就是个神话。你讲的故事,从一开始就站不住脚。” 戴海燕见我不说话,接着说:“你还说,王世贞毒杀严世藩,是因为自己的父亲王忬被严嵩所杀,但王忬死在嘉靖三十九年十月初一,王世贞扶棺返回老家江苏太仓,是在十一月二十七日,从此一直隐居,到隆庆二年才出来做官。而严嵩在嘉靖四十一年倒台后,严世藩被发配到雷州,中途逃回江西老家分宜,直到四十四年被杀。我问你,在江苏的王世贞,哪来的机会在北京朝堂与在江西的严世藩相见?” 我哑口无言。 “至于什么白衣书生在葬礼上窃走死者一只胳膊和《清明上河图》的其他相关桥段,我都懒得说了。人的臂骨是很结实的,在众目睽睽之下,王世贞居然能迅速锯断死者一只胳膊从容离去,可能吗?” (摘自《古董局中局2:清明上河图之谜》 马伯庸 著) |
|
≡ 洛阳社区最新图片 ≡ | ≡ 洛阳社区热帖 ≡ | ||
≡ 房产家居 ≡≡ 汽车时代 ≡ | ≡ 河洛文苑 ≡≡ 馋猫大本营 ≡ | ≡ 聚焦河洛 ≡≡ 亲子教育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