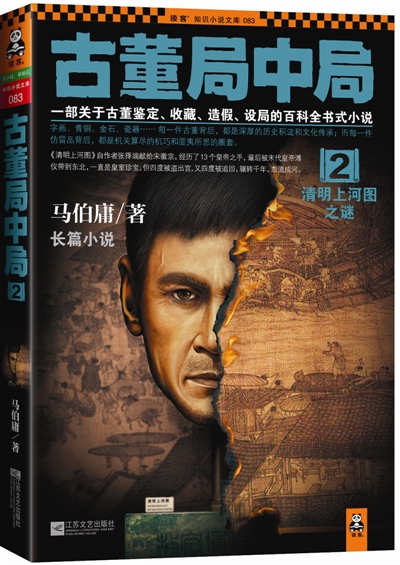|
||||||||||||||
 |
|
|
2013 年 12 月 11 日 星期 三 |
|
||
| 机关算尽 匪夷所思 |
| 44 找到名画残片 |
我把铁盒小心翼翼地捧出来,打开后发现里头是灰白色的骨灰。在骨灰当中有纸灰的痕迹。骨灰和纸灰很容易分辨,骨灰颗粒较大,呈灰白色;纸灰发黑,较为细腻。 我沮丧地一屁股坐在草地上,胸中郁闷无比。在失魂落魄时我右手一歪,盒子朝一侧倾斜,忽然,我看到在盒子的灰烬中似乎多了一样东西。我睁大了眼睛,看到那是一块枯黄的东西。我屏住呼吸,用随身带的镊子轻轻地夹出了一块小绢片。 这块绢片只有婴儿手掌那么大,埋在盒子的最底下。它的形状很不规则,边缘发黑并卷起,显然是火烧成的。我夹起绢片,对着阳光看去,只见这块绢片绢质老旧,上有暗红色的双龙印记,绢面上还有几滴像眼泪一样的痕迹。 没错,就是它,这就是自明代以来就失踪了的《清明上河图》的残本余片,这就是最关键的证据。 原来,廖定和《及春踏花图》是被分开烧的。廖家在开封先将廖定火化,骨灰带到北京在灵山这里下葬。在骨灰盒埋下去之前,把《及春踏花图》的碎绢片点燃扔进盒子里。 那几滴眼泪状的东西叫作烛泪。书画在重裱的时候,要加胶、加矾、加蜡,把背面轧出光来。书画重裱次数多了,侧看绢面会有一层淡淡的光,这叫镜面,也叫鉴云。这块带着双龙小印的绢片本来是属于《清明上河图》的,被补缀到《及春踏花图》上以后,还特意轧过几次。在《及春踏花图》的碎片燃烧之时,绢面的胶、矾、蜡起了保护作用,加上盒子一盖,里面空气稀薄,使得这一片画没有完全燃烧,蜡融化之后,就留下了眼泪一样的痕迹。 造假者本意是为了修补破绽,却无意中保护了原作。《及春踏花图》的其他部分都被烧成了灰,偏偏这一块因为抹过了蜡而幸存下来。 刘一鸣说得不错,人可鉴古物,古物亦可鉴人。 这幅赝品鉴出了我爷爷许一城的坦荡胸襟,鉴出了廖定的忠义,也鉴出了我内心深处的希冀——我的家人从来没有抛弃我,他们一直在我身边。不然实在无法解释,为何我一直苦苦追寻的东西,会藏身于许家四位成员埋葬的墓园附近。 我跪在地上,在许一城被处决的刑场旁,在埋葬着我所有亲人的墓园旁号啕大哭。那一刻,我就像是回到了自己真正的家一样,每个人都在,他们都面带微笑看着我,叫着我的名字。 天空变得更蓝了,几片白云悄然飘过,为我遮去了炽热的阳光。 香港和北京真是不一样。这是我第一次到香港,我注意到,在湾仔香港会展中心京港文化交流文物展展厅的通道两侧,已经张贴了许多海报,而《清明上河图》占据了最显眼的位置。虽说距离文物展还有3天,但这里的气氛已经很火热了。 这时一个车队耀武扬威地停到了文物展展厅的大门前,这个车队的车都是大头宾士和劳斯莱斯。这时第二辆车停在我前面,从车上下来一个中年人,大背头,其穿着打扮就像电影里那些黑社会的老大一样。 “许先生,欢迎欢迎。”中年人热情地朝我伸出手,操着一口生硬的普通话。他见我在原地没动,拍拍头:“哎呀,忘了自我介绍了,我叫王中治,百瑞莲的香港负责人。这次听说您来香港,我们百瑞莲准备了接风宴,请您务必赏光。” 我后退一步,不动声色地端详着王中治,说:“不好意思,我还有点事,先走了。” 王中治连忙说:“有什么事?可以坐我的车去,我陪你。在香港,没有我办不了的事。” “呵呵,不用了。”我委婉地回绝他,继续朝前走去。王中治一把拉住我的胳膊,脸色阴沉地说:“许先生,你也许没听懂我的意思。在香港,没有我办不了的事。” “哦,那还真是让人佩服。”我说。 (摘自《古董局中局2:清明上河图之谜》 马伯庸 著) |
|
≡ 洛阳社区最新图片 ≡ | ≡ 洛阳社区热帖 ≡ | ||
≡ 房产家居 ≡≡ 汽车时代 ≡ | ≡ 河洛文苑 ≡≡ 馋猫大本营 ≡ | ≡ 聚焦河洛 ≡≡ 亲子教育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