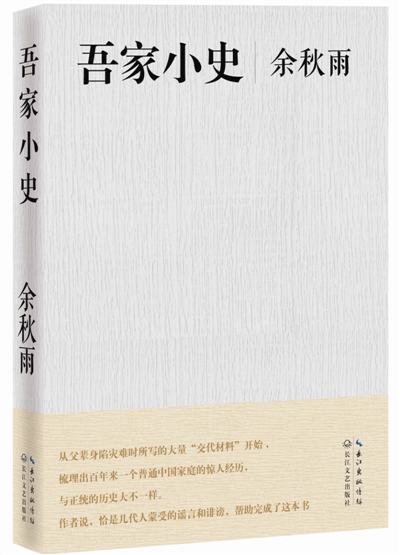|
||||||||||||||
 |
|
|
2014 年 3 月 6 日 星期 四 |
|
||
| 自家小史 娓娓道来 |
| 05 《红楼梦》,同性恋? |
这个地区的领导人就是叔叔的老朋友江斯达。当时江斯达还没有被打倒,为了不让造反派的矛头指向自己,他出席了第一次批斗叔叔的会议。这次批斗会的主题是“狠批封建主义大毒草《红楼梦》”。当时,无论是造反派还是江斯达,都不知道毛泽东喜欢《红楼梦》。当然,我叔叔也不知道。 按照惯例,批判一定引来揭发,一个与叔叔同样着迷《红楼梦》的朋友在会上高声揭发,他说叔叔曾在一次读书会上说,《红楼梦》的主角贾宝玉与书中写到的一位演员蒋玉菡,可能是同性恋。当时的中国人基本不了解同性恋,断定叔叔在散布下流色情信息。 叔叔被拉上了一辆垃圾车,挂着牌子游街示众。牌子上写着六个字:“《红楼梦》,同性恋。”在当时,民众看人游街示众是一件乐事,每一次都人山人海,他们一个个踮着脚,伸着脖子,指指点点,像过节一般。很爱干净的叔叔坐在垃圾车上被那么多人围观,他觉得是奇耻大辱,便把头低下,却不小心发现街角有一个年轻女子也在看他。 这位年轻女子,就是叔叔给妈妈提到过的那位演员。此刻她态度冷漠,没怎么看叔叔的脸,却目不转睛地看着叔叔胸前牌子上的六个字。 叔叔的目光快速从这个女子身上移开,心想幸好这个女子最近没有来给自己洗衣刷鞋。叔叔抬头注视街边密密麻麻的民众,突然不觉得有什么奇耻大辱了。 叔叔从上海西郊一个丹麦人住宅的地下酒窖出发来到这里,家里的亲人都不知道这里什么样,却都知道这是他待的地方。他为这里的民众做了多少事,这个秘密只有一个人清楚,那就是江斯达。但前几年,他又为了这里的民众,把这个人得罪了。他冒险上书北京,只想把这里的民众拉出灾难,但眼下,他们全都兴高采烈围观他,他陷入了灾难。他闭上了眼,任垃圾车摇摇晃晃,满脑子都是那个丹麦人住宅的地下酒窖。 叔叔那天晚上就割腕自杀。那个揭发他的朋友正从窗前走过,发现情况不对,与别人一起破门而入,把叔叔送到了医院。抢救回来才三天,叔叔第二次割腕,又被抢救,因此有了第三次割腕。 叔叔是一个血性男子,壮怀激烈。他三次割腕,完成了三次最决绝的政治抗议和文化抗议。他让我想到我们的余家先祖,在一片血泊中举起了最后那面旗。 后来马兰听我讲叔叔在安徽自杀的事,每次都忧心忡忡。她觉得,应该为叔叔做点事。 “他太孤独了。”马兰说,“这片土地不应该这么对待他。” 就在叔叔去世二十五周年的祭日里,黄梅戏《红楼梦》在安徽隆重首演,产生了爆炸般的轰动效应。这出戏获得了全国所有的戏剧最高奖项,在海内外任何一座城市演出时都刮起了旋风。 在全剧的最后一幕,马兰跪行在台上演唱我写的那一长段唱词时,膝盖被磨破了,鲜血淋漓,她的手指也拍击得节节红肿,每场演出都是这样。 所有的观众都在流泪、鼓掌,但只有我听得懂她的潜台词:刚烈的长辈,您听到了吗?这儿在演《红楼梦》! (摘自《吾家小史》 作者 余秋雨) |
|
≡ 洛阳社区最新图片 ≡ | ≡ 洛阳社区热帖 ≡ | ||
≡ 房产家居 ≡≡ 汽车时代 ≡ | ≡ 河洛文苑 ≡≡ 馋猫大本营 ≡ | ≡ 聚焦河洛 ≡≡ 亲子教育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