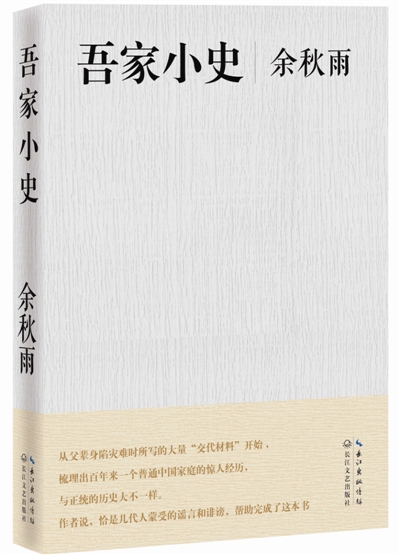|
||||||||||||||
 |
|
|
2014 年 3 月 7 日 星期 五 |
|
||
| 自家小史 娓娓道来 |
| 06 妓女,“文化口红” |
突然,有一位年轻的女读者走到我跟前停下,看了我一眼,低下头说:“余先生,上海那个人写了一篇不好的文章冒犯你,我向你道歉。” “什么文章?”我问。 “说有一个妓女在读你的《文化苦旅》。”她声音很低,快速说完后转身就走了。 她相当俏丽,很有风韵,把我们三个人的目光都吸引住了。我们看着亭亭玉立的她行进在修剪得很好的灌木之间,又消失在图书馆门口。 “文章又不是她写的,她为什么要道歉?”我问。 “有三种可能。”杨长勋说,“第一种可能,她是那个作者的家人或朋友;第二种可能,她只是你的读者,觉得你是因为受读者欢迎才受攻击的;至于第三种可能,就不好说了……” “说!”我命令他。 “第三种可能,她就是那个妓女。”杨长勋说,“这种可能最大。” 我回想刚才她低头低声、快速离去的样子,也觉得有这个可能,就说:“那她就很高尚。我们谁也不认识她,她也不必道歉,但她道歉了!齐华,你说呢?” 我转身看齐华,发现他还呆呆地看着图书馆的大门。“太像了。”他喃喃地说。 我看着他,立即明白了。刚才我看这个女青年的时候也觉得有些眼熟,不错,她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姜沙,只是小了一代。 “像谁?”杨长勋问我。 “一时说不明白,”我说,“以后慢慢再给你说吧。” “有一个妓女在读《文化苦旅》”,这句话如果是事实,也不至于掀起对《文化苦旅》和作者的声讨吧?但在上海,这种声讨快速形成,并推向全国。 按照“文革”大批判的逻辑,《文化苦旅》转眼上升为“妓女读的书”。我收到大量读者来信,说他们受了污辱,强烈要求我通过官司来为他们讨个“清白”。但我知道,这事打不得官司。难道要法院证明没有妓女读过这本书?我可以肯定,如果要追问那个写文章的上海人:是哪一个妓女?他一定不会说;再问:是否认识那个妓女?关系如何?他也不会说。 谢晋导演气鼓鼓地找到我,大声为我辩护,说中外历史上很多妓女的人品、文品都很高,为此,他还要拍电影来表现她们。我很感谢这位大导演,但也明白他的辩护思路错了。 这件事情的特殊意义,是突然唤醒了上海街市间曾经忙碌了一百多年的小报文痞、情色讼笔。那个被我绝交的“左派”编剧更是兴奋,觉得终于等到了给我“写回信”的机会。他十分内行地分析,妓女的手提包里一定放有口红,既然口红和《文化苦旅》联系在了一起,它也就成了“文化口红”。从此,很长时间,批判“文化口红”成了他的主业之一。 当时的上海文坛,除了谢晋导演继续气鼓鼓地毫无办法,百岁老人巴金躺在病榻上也遭受到报刊的辱骂,而他还在听人朗读我的书,我的那些“文化口红”。黄佐临先生则给我留下了“让他们骂去”的遗言,告别了人世。再也没有人理会这些过时的人,大家热衷关注的,还是妓女、口红,口红、妓女……洋溢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欢快。 事情看来不大,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我看了一阵,得出一个结论:上海,真的必须离开了。 (摘自《吾家小史》 作者 余秋雨) |
|
≡ 洛阳社区最新图片 ≡ | ≡ 洛阳社区热帖 ≡ | ||
≡ 房产家居 ≡≡ 汽车时代 ≡ | ≡ 河洛文苑 ≡≡ 馋猫大本营 ≡ | ≡ 聚焦河洛 ≡≡ 亲子教育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