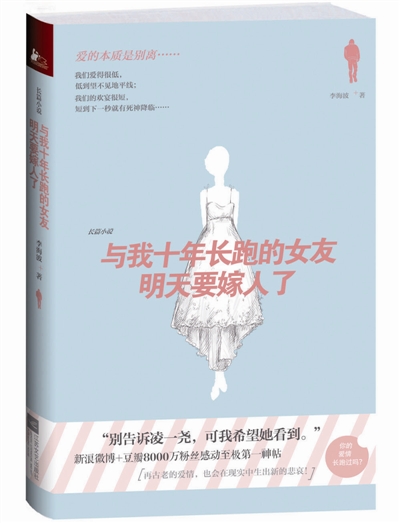|
||||||||||||||||
 |
|
|
2013 年 11 月 29 日 星期 五 |
|
||
| 爱情长跑 催人泪下 |
| 33 准备去新疆 |
我想得非常清楚,凌一尧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女儿嫁得好,不愿让她浪费青春,这些都是人之常情。 那段日子,我对金钱无比痛恨,也对金钱无比向往。 我给老刘打电话,说:“哥,那事儿我想好了。” “怎么样呢?” “我跟你一起去新疆。” “确定了?” “嗯。” 老刘忽然想起什么,说:“你记得老赵吧?去年围海工程的合伙人之一。” “记得。” “他对去年的分红比例不满意,这次他不想入股了,我们也不想带他一起干。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可以跟其他合伙人谈谈,让你填补老赵的空缺,参一个小股,怎么样?” 我几乎没有犹豫,一口答应下来:“好的。” “你能拿多少钱出来?” “我有20万元,可以全部拿出来。”我说。 事到如今我只有孤注一掷,我连凌一尧都快输了,还有什么输不起的? 当天晚上,我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父母,他们非常惊诧,不理解我为什么要跑那么远,我妈更是极力反对。 “我都26岁了,你们担心那么多干吗?” 我妈说:“别说26岁,就算62岁又怎么样?只要你一天没结婚,在我们眼里你依然是个孩子。” “今年我在新疆那边不只是打工,手里的20万元都准备拿去参股,虽然少了一点儿,但至少是一个小股东。” “20万元?”我妈顿时瞪大双眼,“你辛辛苦苦攒下这点钱,干吗一下子全投进去?” “这点存款不可能吃一辈子,投资不嫌多只怕少,有多少种子才能打多少粮。” 我妈心事重重地搁下碗筷,又自责道:“你要是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就不用这么拼命了。” 我笑着安慰她说:“我要是出生在别的家庭,那另一个孩子就要出生在这里,到时候你还是会心疼那个儿子。再说了,你们把我拉扯这么大,我四肢健壮,智商超群,已经相当了不起了。” 我爸也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年轻人吃苦耐劳,愿意自己出去闯一片天下总归是一件好事。” 自从上次与凌一尧的父亲见面以后,我没有再主动与她联系,即便她主动打电话过来,我也刻意表现出冷漠的样子。没有争吵,没有亲昵,也没有将她父亲约我见面的事情告诉她,把那口怨气留在自己心里慢慢消化。但我越是这样,凌一尧越是焦急,认为我心灰意冷,或是移情别恋,在电话里吵得更凶了。 “吕钦扬,我们明天见面吧。”她说。 “见面又能怎么样?既然你爸妈给你安排了一个美满的未来,那就试着接受吧,兴许没多久你就适应了。” 凌一尧难以置信地问:“你不想和我在一起了?” “当然不是。”我下意识地予以否认,沉默片刻才解释道,“我们相处这么多年,无论过得好或者不好,开心或者不开心,都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现在突然多出另一个人,我不知道怎么面对,宁可把你拱手让给他,也不愿让你变成一个脚踩两条船的女孩。” “你以为你这样很伟大?”她有些气愤。 我一时语塞,因为我也无法说清自己是否存在这样虚伪的想法。 “我既不是商品,也不是礼物,你凭什么想让给谁就让给谁?我妈都气得住院了,亲戚朋友也说三道四,但我还是想和你一起抗争下去,从未想过动摇。” 她在电话里越说越委屈,悲伤地抽泣,努力压抑着声音,似乎担心被家人听见。我默默地听着,心口一阵阵地疼痛,却又束手无策——她这样执着地站在我这边,而我只能像她父亲说的那样,让她承受不必要的痛苦,奔赴不可知的前途。 “你到底在想什么?”她问。 我叹息一声,说:“哪有资格想什么,想不到一下子冒出来这么多敌人,好像自己在被所有人欺负。” 凌一尧止住哭泣,责问道:“难道我也欺负你了?” “我没说你。” “你就是太不自信,那些不在乎你的人,你何必在乎他们的看法?” (摘自《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 李海波 著) |
|
≡ 洛阳社区最新图片 ≡ | ≡ 洛阳社区热帖 ≡ | ||
≡ 房产家居 ≡≡ 汽车时代 ≡ | ≡ 河洛文苑 ≡≡ 馋猫大本营 ≡ | ≡ 聚焦河洛 ≡≡ 亲子教育 ≡ | |